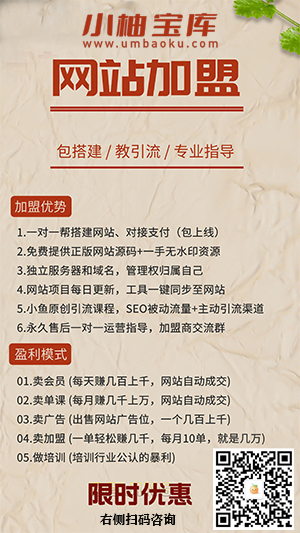位于沂南县砖埠镇孙家黄疃村的“诸葛亮故里纪念馆”是1993年建成开馆的。
九十年代初是一个财力物力尚且贫乏的年代,在一个老村中建造这么一个古建样式的院落,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方面建设场地关系着村里十几户村民的搬迁,另一方面建设资金也是遥不可及。但就是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诸葛亮故里纪念馆还是如期建成了。
今天我在孙家黄疃村走访,听村中老人们回忆讲述纪念馆的建设过程。感叹参入者建设者的一腔热情,感叹当时那一段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
是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天时,是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大的环境,是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文化复兴和“诸葛亮热”。
地利,是阳都故城遗址的再一次被公众认知,以及阳都大地上黄疃庄、任家庄、殷家庄、大小汪家庄等相关村庄的密切配合。
人和,是当时省、县、乡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关心关怀;以黄疃孙元吉、浙江兰溪诸葛镇诸葛绍贤等民间有识之士的热情联络推动;乡里乡亲满怀自豪感的积极参入和孙家黄疃支部书记高庚兴等一班人的朴实能干;还有以大汪家庄创业型企业家代表汪立志等人士的无私奉献。
一封来自于浙江兰溪诸葛镇的寻根信
1991年8月,沂南县砖埠乡孙家黄疃村收到了一封来自于浙江省兰溪市诸葛镇大公堂理事会的信件。
村支部书记高庚兴收到这封信以后,拆信一看,看出是外地的诸葛亮后人的寻根问祖的信件,就马上拿给孙元吉看。孙元吉先生是一位退休干部,从县机关上退休后一直在老家居住。村里人都知道孙元吉是一位诸葛亮研究的专家,在县里、省里都有很大名气。
这封来信,信封上写的收信人地址是“山东省临沂市(或沂南县)诸葛城(镇)诸葛村委会 收”。沂南县显然是没有诸葛城或者是诸葛村,来信这样写,也显然是一种投石问路的表现。就是在不能确认有没有诸葛城或者诸葛村的情况下,“有枣没枣打上一杆子”。
写的是“诸葛村委会收”,信件却被投送到孙家黄疃村里来,这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已经有了一种“阳都故城遗址在砖埠,诸葛亮老家在孙家黄疃一带”的普遍认知。
信件是一个叫“诸葛绍贤”的诸葛亮后人写的,他首先说明了他们兰溪市诸葛镇的所在地和所处位置,又简要说明了他们诸葛镇诸葛族人是诸葛亮嫡系后裔的源流,表明了急切地想寻找到诸葛亮故里以及诸葛氏老家诸葛氏宗亲的情况。
信中还说,他们曾经在1990年给沂水县诸葛镇写了信,但是没有得到回音。这次是写了三封信,分别寄给沂水、临沂、沂南,并且说明“是以投石问路的形式,不管对否有劳答复。有必要我们会派人前来谒祖,以便证实来龙去脉,并盼望宗亲能派人到我们这里参观游览,我们当扫榻茶迎。附三份启事,特请过目,并望即日赐教为盼”。
信的末尾,又特别注明“我们寄奉大公堂启事书三份,是告诉你们,我们浙江省兰溪市诸葛镇这一支诸葛氏族,确系武侯公嫡系裔孙。告诉来龙去脉,并不是向你们求援资助,请勿误会为盼。”
孙元吉先生看到这封信后,马上意识到诸葛亮后人的来信非常重要。他随即就给写了回信,说明了关于阳国、阳都、阳都故城遗址所在地和诸葛亮出生于阳都等情况,并且说明了诸葛亮故里诸葛氏族的现状和移迁分布等情况。
回信后,兰溪诸葛氏马上就有了再次来信,他们对寻根有果非常高兴。自此以后,孙元吉先生和诸葛绍贤先生信函频繁,有了深入的交流。
当年秋天,兰溪诸葛绍贤、诸葛达等四位先生带着《诸葛氏宗谱》来到了沂南踏上了阳都故土。孙元吉先生在及时向乡里、县里汇报的同时,设家宴热情招待了远方来宾。
热心人孙元吉先生
黄疃村的老人们都说,诸葛亮故里纪念馆的建设,是孙元吉热心推动才促成的。没有他的上下联络,纪念馆不可能建设和建成。
孙元吉老人是我尊敬的长者,十几年之前我行走阳都故城村庄,有一次曾经天晚不能归、夜宿黄疃庄,在老先生跟前潜心问道促膝长谈。他曾经向我亲口讲述了当时诸葛亮故里纪念馆建设的前前后后的情况。
与诸葛亮后裔有了联系后,孙元吉先生就有了马上启动建设诸葛亮纪念馆的想法。
当时启动纪念馆建设,有着许多的有利因素。一是县乡领导对诸葛亮文化研究弘扬的重视。当时,一大批有学历、有文化的知识型干部走上了政治舞台。县五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同志牛泉然、黄宜全、魏延端、刘振邦、范恩义等,都是高学历干部。他们重视文化、重视诸葛亮文化的发掘开发。二是活跃的历史文化研究氛围。县政协文史委、县志办等史料史志办事机构,把重点放在了阳都故城考究、诸葛亮研究和红色文化发掘整理之上。孙元吉、李彦修、张建国、郭善勤等一大批文史爱好者研究者,乃至于临沂城里的王汝涛、刘家骥、王瑞功、唐士文等专家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著述和传播。三是深厚的群众认知度和高昂的参入热情。“阳都故城在沂南”、“诸葛亮老家是沂南”的意识,已经为广大民众所普遍认知,人们充满了自豪感和参入的积极性。
正是对形势有着准确的把握,孙元吉先生早就有了在阳都故城遗址上为诸葛亮建个纪念馆的想法。浙江兰溪诸葛亮后人的来信和与诸葛亮后人的交流,使孙元吉先生更加有了时不我待的意识。
主意已定,孙元吉老先生在向村里干部们提出并分析这一建议的同时,马上启动了向上级领导的请示汇报工作。他的建议得到了县里领导的高度评价,领导们不但答应批拨一定数量的政府资金支持,还积极地向省市领导汇报。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李子超同志,十分关心沂南老家的诸葛亮文化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指导和支持。
争取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孙元吉先生又发动了村里一班人进行具体实施工作。当时孙家黄疃村委一班人高庚兴、孙振吉、孙元京、孙延征、孙起信等,热情高、干劲大,他们有决心有信心把诸葛亮故里纪念馆建起来。
艰难的建设过程
纪念馆的场地,规划在了孙家黄疃老村西北片的大白果树附近。之所以规划在这里,一是清朝《沂水县志》记载“沂邑南,河阳村南十余里,沂水西岸半里许,桑泉水南五里黄疃庄,阳都城故址犹在。”二是这里大白果树下是一个古老的庙宇旧址,传说这个庙宇最早就是“诸葛亮家庙”或者“诸葛亮庙”,是诸葛氏的祠堂或者是前朝老代祭祀诸葛亮的地方。
建设面临的首要困难就是老住户的搬迁。白果树下,除了老庙基础上建设的学校几间旧房以外,白果树附近南北两个胡同、东西四条小巷子,十五家老住户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老房家院是他们赖以生活的根本。十五户人家拆迁,必须给他们找到住的地方。以村支部书记高庚兴为主的村班子,经过了多次讨论,商量好了拆迁方案补偿办法,公布于众,得到了村民们的普遍好评和积极响应。
按照建设时间计划,住户必须马上搬迁,等不得建成新的居住安置房屋。村干部们积极地想办法,为搬迁户腾出、修缮安排了仅有的所有能够住人的周转用房。
十五户老居民,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拖后腿,在尽短的时间内全部搬迁完毕。其中,这十五户住宅家院,就有两个是支部书记高庚兴家的。
住户迁走后马上拆除旧房,拆迁垃圾填在了孙家黄疃和高家黄疃两村之间的大水汪东侧,造出了两村之间的一条便捷通道。
平整场地的同时,孙元吉、高庚兴和乡领导赵宗仁一行三人踏上了到浙江兰溪学习取经的行程。在兰溪诸葛长乐村(也叫高隆岗村、诸葛八卦村),他们看到了那里的风貌别致的老村古建,看到了人们对诸葛亮的敬仰和虔诚,看到了依托诸葛亮文化资源红红火火的古村旅游,看到了文化旅游资源带给村里人大把的票子和富足的生活。
这次考察,村里没花一分钱,车辆和所有的费用都是大汪家庄汪立志创办的“三建公司”出的钱。三建公司给准备了5000元现金。为了节省开支,他们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来回几千里的行程仅仅花了一千多元。当然,诸葛八卦村诸葛亮后人管吃管住热情接待,也为他们节省了部分费用。节余下的现金,他们又一分不落地交回了三建公司。
当时,兰溪诸葛八卦村刚刚完成了诸葛大公堂重修工程。八卦村人从建筑风格、规划设计、资金筹措等,给与了他们全方面的经验指导。学习考察的结果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更加具有了建设好诸葛亮故里纪念馆的办法。
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按照原来的规划,诸葛亮故里纪念馆要建设两进院的前后两个大殿,预算资金六七十万元。多方筹措的资金很多还是“纸上画饼”没到位的时候,建设工程则如期紧张开工了。承担建筑施工的“三建公司”经理汪立志先生明知道这是一个不挣钱甚至是赔本的项目,但没有一点推却。而是本着“只能建好,不能建孬”的原则,全力投入了备料施工。
为了建好,没有任何古建筑建造经验的“三建公司”派出技术人员到曲阜孔府考察学习。建筑用砖用瓦等主辅用材全部讲究正宗,资金没来就垫资建设。为了坚实耐看,45公分厚的院墙一点也不能含糊,绝对要分毫不差。
上级支持的资金迟迟不到位,村里人不等不靠自己积极地想办法。村里人把满河滩的树木伐掉换了十几万元钱,建设拆迁户住房以外,全部投入了纪念馆建设工程。
由于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资金紧张,特别是乡级政府资金困乏,乡里连筹集买个时兴的“跑不死的桑塔纳”的钱都没有。工程将近完工时,许多的答应好的资金也没到位。承建人慷慨捐助了十万元资金才得以竣工。
1992年底,大殿、院落修成,随即进行了诸葛亮神像的塑设和置花种草的庭院美化。孙元吉先生还把多年在阳都故城遗址上收集珍藏的一些古砖老瓦、罐鬲陶器、画像石等陈列其中。李子超同志欣然为“诸葛亮故里纪念馆”题写了馆名,书法家姜东舒为大殿题写了“地灵人杰”的匾额,王汝涛先生豪情以歌《望海潮》为颂,书法家魏启后书妙语楹联“沂汶蒙三水环绕圣贤地,秦汉唐一脉相承阳都风”。大殿辉煌,熠熠生辉,庭院寂寂,满目庄严。千年银杏树青春焕发,阳都大地生机勃勃。
当此之时,沂南县城界湖西山上的“诸葛亮铜像”也塑设完成不久。阳都故土上诸葛亮神像肃然,县城西山诸葛亮坐像灵动。整个的沂南,被诸葛亮文化笼罩浸染。
1993年古历的4月14日诸葛亮诞辰纪念日,开馆仪式如期举行。各级领导前来出席,各方来宾盈盈满堂。诸葛亮后人兰溪诸葛绍贤、诸葛向华、诸葛坤亨,南韩诸葛明等众欣然来贺。
从黄疃出发的“诸葛亮文化之旅”
2011年3月29日,沂南组织了一支寻访队伍,从黄疃诸葛亮故里纪念馆出发,开始了几千公里的“沿着诸葛亮足迹,诸葛亮文化之旅”的行程。
诸葛亮是14岁离开老家沂南流徙四方的。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沿着诸葛亮远游的路线地点,先九江,再南阳,再荆州,再川蜀,再秦岭,再五丈原,一路探寻他的踪迹。但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各方面限制,梦想一直未能实现。
感谢好友朱茂强的用心联络和谋划,这年的春风里,我们12人组队的探访活动终于成行。
启程以前,孙家黄疃村的老人们在阳都故城遗址上焚香化纸,隆重地捧满一兜一兜乡土,让我们带给沿路的各个诸葛亮奉祀纪念地留存。
一路走来,我看到了南阳中原人的豪放,见识了襄阳人的儒雅,品味了岐山塬上的臊子面,体会了锦里成都人的慢节奏和悠闲,也看到了沔水边阳平关人的机警多诈。
我们也到了兰溪诸葛八卦村,深刻体味了诸葛亮后人的热情好客。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沂南人到了这些地方,人家都是那么礼遇那么热情,这是为什么?用心体会,这才想到是因为我们一直沐浴在诸葛亮他老人家的光辉里啊。
还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南阳人和襄阳人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在南阳,南阳人坚信诸葛亮是在卧龙岗上“躬耕垄亩”的。在襄阳,襄阳人又坚定说诸葛亮是在隆中结庐居住并“草庐妙对”的。
谁是谁非?个人粗浅认识,感觉古隆中那个山谷,俺的老乡亲诸葛亮确实住过。东汉南阳的辖域和邓县襄阳的地属,不难看出“躬耕南阳”所指地点的统一性。
这一点,我曾经向两方的专家们请教过。在这里我又这样说,南阳的朋友们一定不高兴了。南阳的学者专家们一定又会拿出颠仆不灭的证据把我打得鼻青脸肿满地找牙。
窃以为南阳和襄阳的“躬耕地之争”,本就是“诸葛亮光芒之争”。从明代以来的两地专家们对此的争执,已经远远超出了追求历史真相的本质意义。怨就怨俺沂南家的诸葛亮太优秀太智慧太完人!
还是借用咸丰年间南阳知府顾家衡的妙联来说这个事比较好,那就是“人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南阳襄阳”。
对于南阳襄阳之辩,我们沂南人且不管她。作为“诸葛亮出生在琅琊阳都就是现在的沂南县”“天下诸葛出阳都”的观念是钉子砸在木头里的公认的史实。这也佐证了在沂南在阳都故城遗址上修建“诸葛亮故里纪念馆”的意义非凡。

2月16日星期六上午我冒着寒风来到位于砖埠镇孙家黄疃的“诸葛亮故里纪念馆”。

一进了院子就闻到了扑鼻的腊梅香气,二十多年前栽植的腊梅枝条,已经长成了粗粗的树木。

西南角的千年银杏树上,挂满了红布条。

春节后附近的村民来游玩,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小孩子学生等常来诸葛亮神像前祭拜,据说能够带来聪明带来好的学业和学习成绩。

纪念馆的管理员孙振光正在为游客讲解馆藏汉画像石。

管理员高庚兴正在为客人们解说阳都城诸葛亮故事。

迎门处的著名的四面画像汉碑,已经用碑亭和玻璃板封存。古碑上部带穿,四面雕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画像。
村里老人们说,自古以来这面古碑就站立在大白果树下的老庙一角,穿孔和顶部已经被世世代代的村里人抚摸的很光滑。
1985年,从安徽阜阳来了几个人,出价8万元想着拉走这面石碑。当时的支部书记高庚兴坚决地予以拒绝。八十年代的八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当我问高庚兴当时为什么没有卖掉时,高庚兴说,这面古碑是属于孙家黄疃村的,属于全体村民的。村里人世世代代看着这面石碑,从感情上来说就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绝对不能卖掉。
感谢高庚兴!是他留住了这面具有巨大文物价值的阳都故城遗址上的古碑。也感谢孙元吉等纪念馆的建设者们,因为有了纪念馆的保护,才不至于使这面古碑在近二十余年里没有被贼人偷走。

右侧的画像石碑亭。


为两位老哥留个影做纪念。

我也照了像,权且在大门口在大白果树下留下今天的行走记忆。(孙振光摄影)

宽厚的院墙、高耸的门楼,显示着肃穆庄严。

纪念馆西墙外的空地小广场,

院墙西面是“诸葛故里人才展”,展示了近些年来从阳都乡土上走出去的优秀学子代表人物。
这真是一个好的创意!
砖埠中学很出名,砖埠的学生很出名。这些年来从沂南考出去的北大清华学生,山东、临沂、沂南的高考状元,以砖埠镇的居多。沂南人都说“人家砖埠镇是诸葛亮的老家,出息的学生自然是聪明无比。”


苏家庄子的苏彦祝!

佛谢村的薛梅!山东省文科状元!

西岳庄的白洪娟!山东省文科状元!(图片前有树木遮挡)

南薛庄的石磊!

孙家黄疃的高永强!
还有高家黄疃的高勇,璞头山湖的刘欣一,洙阳村的张明波,砖埠中学的沈德梅,庄家村的丁立彦,南黄埠村的龙云,砖埠子的李善欣,里宏村的张安良,榆林村的李加强等等。
一个个优秀的学子的形象展示在老家的村头,给老家人以自豪,给后学们以激励!给外地人以震撼!

纪念馆西墙

小广场北部有诸葛亮塑像。塑像和一个老石碾组合,显得很有趣味。

村头路口到处是关于诸葛亮的文字,诸葛亮元素充满了村头巷尾。

书法也是很有味道的

村头的老人们向我讲述了很多关于村庄、关于诸葛亮纪念馆建设的旧事。

位于孙家黄疃老村西北部的“诸葛社区服务中心”和新村住宅楼片区。


日东高速公路从孙家黄疃老村北侧通过,也就是阳都故城遗址上传说中的“城南头”外通过。


孙家黄疃老村与任家庄村之间的阳都故城遗址核心区里,除了蔬菜大棚就是零零散散的房屋院落。
十几年前我在这片土地上行走,还见到了田间地头堆积的瓦砾片子等,现在只有零星的所见。

阳都故城遗址区和孙家黄疃村紧邻沂河。

滨河大道从村东通过。老人们说,这滨河大道路基之下,就是老村的根本片区所在。

宽阔的大沂河,露出了岩石河底。老人们说,二三十年前,河床里还是满河的大沙滩,现在的河底,已经抽沙去除了四五米厚的白沙层。
哲学书上说“人不能两次踏过同一条河流”,是说的物质的运动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沂河,也一定不是1800多年前诸葛亮所看到的沂河了。但以物质的恒定性来说,这就是养育诸葛亮的沂河啊。

对岸是东岸滨河大道和坊前、里甲庄子等村。古来孙家黄疃和坊前村之间有着一个渡口。

北望是高速路过河大桥

河岸已经多被砌石加固

河边遗留的土质崖岸。老人们说,过去在崖岸上经常发现被洪水冲出来的陶器、瓮棺、铜箭头等古董物件。

现在还有机器动力渡船在使用着。

孙起文大哥一家是几代老船工了,且听听他的的方言土语吧。1800年前的诸葛亮说话可能就是这种音韵声调。

北边的任家庄东侧,新建了一个拦河坝大水库。

沂河岸上遗留的土坝,是拦蓄洪水用的。据老人们说,老社会的时候,沿河岸上就有一道不高的土坝,1957年发了大洪水,老土坝全被冲毁。这条土坝是1957年洪水过后修筑的,从里宏袁家庄子大堤向南,过殷家庄、任家庄、黄疃、季家庄、梁家庄子、沙沟,一直到了榆林村东。
十几年前我沿着土坝走过,那时的土坝还是基本留存的。滨河大道修建时,多是以土坝为基的。

土坝后来是作为道路使用的,现在也荒草萋萋没有人走了。

从滨河大道上看到的纪念馆,纪念馆东南部和东部曾经是孙家黄疃村老村的集中区片所在。

这个是在老村基础上平整出的停车场。

老村遗留的河边巷口

很少的老村老院遗留

前边紧邻着高家黄疃村

村前小庙

孙家黄疃和高家黄疃两个黄疃之间的大水汪。

大水汪东侧的道路就是修建纪念馆时的拆建垃圾填出来的。

黄疃村西公路

村口的孙家黄疃村碑。
村碑文字:据说雨季沂河水常携带泥沙上岸,洪水过后黄泥淤积,故名黄疃。明初孙氏自山西老鸹窝迁此定居,遂名孙家黄疃。此地系阳都故城遗址。——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东汉光和四年(181年)就诞生在这里。
孙家黄疃村委会 1992年立
孙家黄疃和高家黄疃传说最早就是一个村,当地俗称“黄疃庄”。分成高家、孙家两个黄疃,是明朝以来三四百年以来的事情。

由孙元吉撰文、魏延端书写的“诸葛亮故居”刻石,原立在村北“城南头”地块,现在迁立在了诸葛亮故里纪念馆的南墙外大白果树下。

夕阳下的诸葛亮故里纪念馆有了一种沧桑感。
以上是今天的行走所见纪实图片。
下面放上一组前些年的老照片,看官们可以看一看这里近些年的变化。

“诸葛亮故居”刻石原在的地方。

2011年的南行取土仪式,就是在“诸葛亮故居”刻石旁边进行的。



村里的老人们手捧黄土装满一个个布兜。





乡亲们扎起彩门为我们送行。




浙江兰溪诸葛镇烟雨里的诸葛八卦村


留赠阳都乡土


八卦村的街巷

满村都是风格别致的老建筑。

高隆岗下的农田

诸葛坤亨先生向寻访组两位美女斟酒,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们。

诸葛八卦村的饭菜也都有着有关诸葛亮的命名。

金童玉女组合

阳都故城刻石原在院西小广场

纪念馆后边拆迁后的片区

老村里狭窄的小巷


村中老碾处

七八年前拍摄的孩子们也该上大学了


近观古碑

纪念馆里收藏展示的阳都故城遗址上出土的陶器

滨河大道路基修造时的景象

沿河土坝道路

满地的老砖

瓦砾片子到处都是

十年前的阳都故城遗址核心区域面貌

阳都故城保护碑


娘娘庙旧址旧貌

纪念馆东面河岸上的石墙出口

从河滩里看到的河岸上的孙家黄疃村

老村街道

老村里居住的孙振沂老人


沂河里摆渡的竹篙木船

高速路桥墩下冬季的过河季节性路桥

在梁家庄子村前巧遇孙元吉老人

向学生们实地介绍阳都故城遗址的孙元吉老人


听孙元吉老人讲述阳都故城和诸葛亮的故事。

孙元吉老人手抄的浙江兰溪诸葛亮后裔族人的来信,上部是信封文字,下面是书信内容。书信原件据说已经交到县里去了。
(该书信抄件,是季家庄刘善军先生保存并提供的。特此感谢。)
限时特惠: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网赚创业教程,会员可以下载全站资源点击查看详情
站长微信:11082411